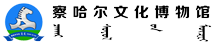编者按:薄音湖,著名蒙古史学者,曾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现为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内蒙古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学术顾问。
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元史,专门史·中国民族史,侧重于明代蒙古史的研究,出版《简明古代蒙古史》、《一代天骄和他的继承者》、《元太祖本传》、《明代蒙古史论》等专著,出版了古籍整理《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二辑。发表论文《达延汗生卒即位年考》、《俺答汗征兀良哈史实》、《俺答汗征卫郭特和撒拉卫郭尔史实》、《俺答汗征卫拉特史实》、《十六世纪末叶西藏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关于北元汗系》、《关于察哈尔史的若干问题》、《明代蒙古的黄毛与红帽兀良哈》、《买的里八剌与脱古思帖木儿》、《明美岱召泰和门石刻考》等50余篇。
数年来,他始终在蒙古史的教学科研岗位上辛勤劳作,为蒙古史研究倾注心血,为国家培养人才竭诚尽力。多次受邀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论坛,曾多次接受国内外各级媒体的采访报道,在传承弘扬蒙古族历史文化,抢救保护珍贵文化遗产,繁荣发展民族文化事业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受到了各级领导和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誉。
社科普及
蒙古史书记载明代蒙古社会组织时,常常采用固定的表述形式。例如以“都沁·都尔本”(dočin,dörden,四十和四,即四十万户东蒙古和四万户西蒙古瓦刺)来概称全体蒙古人;同时又以“六万户"( ǰirγoγan tümen)来概称东蒙古,因为蒙古人认为元朝灭亡后,四十万户蒙古中的三十四万户被留在内地,只有六万户回到北方,这样,加上瓦剌的四万户,全体蒙古人为十个万户;达延汗统一东蒙古建立六万户制,不久六万户之王的兀良哈万户因叛乱而被消灭且被瓜分,尽管六万户只剩下五万户,蒙古人仍然自认为是六万户。他们有时也还自称为四十万户。这里除了达延汗时代确有的军事行政建置六万户之外,都只有观念中的概数,并不能反映蒙古社会组织的发展变化情况。
万户之下诸鄂托克的数目与万户的情形相似,也常常采用固定的表述形式。诸如:察哈尔八鄂托克、外喀尔喀七鄂托克、内喀尔喀五鄂托克、土默特十二鄂托克、鄂尔多斯十二鄂托克(或称八鄂托克)、喀喇沁七鄂托克等等。万户是大的部落集团,鄂托克是万户之下的小部落,如所周知,鄂托克是以人户与牧地分封给黄金家族子弟而形成的,达延汗时期是初次分封,此后随着他的子孙的繁衍,分封不断进行,每个子孙的封地愈来愈小,这些子孙的封地——部落几乎都冠以某个名称,因此,部落的名称也愈来愈多。上述诸万户之下鄂托克的数目,显然不能正确反映鄂托克的发展变化情形,也只是习惯上的概数而已。目前能够明确指出的比较早期的鄂托克,大约只有外喀尔喀七鄂托克和内喀尔喀五鄂托克,即外喀尔喀七鄂托克是由达延汗之子格哷森札所生七子各有封地而形成的,内喀尔喀五鄂托克,是由达延汗之子阿尔楚博罗特之子和尔朔齐哈萨尔(明译虎喇哈赤)所生五子的封地而形成的。其余各万户的鄂托克,日本森川哲雄曾对察哈尔、土默特、鄂尔多斯三个万户的鄂托克做过十分详细的研究有许多有益的成果。但其结论仍不免有不少推测的成分,其原因一是史料记载有许多讹误,而且彼此矛盾,二是鄂托克的数目本来就时有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以固定的眼光去分析这些鄂托克的数目及其名称,不能不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
下面试就察哈尔诸部的一些情况及察哈尔若干部落入清后的结局再做探讨。
关于察哈尔诸部的记载,以《皇明九边考》为最早(嘉靖二十年、1541年成书):北虏亦克罕一部,常住牧此边。兵约五万,为营者五,曰好城察罕儿,曰克什旦,曰卜尔报,东营曰〔召〕阿儿,西营曰把(即)郎阿儿,入寇无常。
稍晚的《皇明北虏考》(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成书)记载同一情况说:众立卜赤,称亦克罕。亦克罕大营五,曰好陈察罕儿,曰召阿儿,曰把郎阿儿,日克什旦,日卜尔报,可五万人。卜赤居中屯牧,五营环卫之。
两书的记载都是反映达延汗之孙博迪汗( Budi gaγan,明译卜赤、不地,亦克罕即大汗之意,约1519-1547年在位)时期的情况。所谓“营”即“鄂托克”。两书所载各有长短,综合起来可以看到、大汗所属的五营,实际上只有三营——好陈察罕儿(Qaγučin čaqar)、克失且( Kešigten,清译克什克腾)、卜尔报。召阿儿(ǰegün γar)指东营,即左翼,把郎阿儿(baraγun γar)指西营,即右翼,显然召阿儿和把郎阿儿都不是具体的营——鄂托克的名称,而是指万户之下的鄂托克左右翼。
再来分析两书所载的召阿儿、把郎阿儿以外的三营。
克什旦(克什克腾)在蒙汉文史书里都说是属于察哈尔,这一名称源于蒙元时期的大汗禁卫军怯薛(复数作怯薛丹,Kešigten)。《蒙古源流》记载达延汗分封诸子时,其子“斡齐尔博罗特(Včir Bolod)统率察哈尔之八鄂托克克什克腾”,《王公表传》说:“元太祖十六世孙鄂齐尔博罗特再传至沙喇勒达,称墨尔根诺颜,号所部曰克什克腾……服属于察哈尔”。作为鄂托克的克什且(克什克腾)的形成,并不在沙喇勒达时代,而是他的高祖齐尔博罗特时代。
卜尔报是罕见的部落名称,和田清在他的研究中对此完全不做分析,森川哲雄在《试论察哈尔八鄂托克及其分封》中认为在蒙文史料中看不到类似的部名,因而怀疑是明人的误记。事实上,在蒙文史料中还是可以看到与卜尔报相应的部名。在佚名《黄金史》中,提到摩伦汗(达延汗的从叔祖)麾下的一名先锋官伯颜乌尔默格尔(Bayan Ürmeger),他属于博尔布克部( Borboγ),后来成为达延汗的将领;达延汗派人追杀仇敌亦思马勒,带兵前去的有博尔布克部的孟克( Borboγ-un Möngke);护送达延汗之子巴尔斯博罗特的七人中,有博尔布克的额勒济格乌尔鲁克(Boboγ-yin Elǰige Örlüg)。罗卜藏丹津《黄金史》中与此相应部分的记载大体相同。在《金轮千辐》记载中,此部是由达延汗之阿尔苏博罗特(Arsubolod)统领的。札奇斯铁认为 Barboγ 似乎就是卜尔报,根据上述Barboγ 屡次作为部名出现以及它的读音与卜尔报相同,我赞同札奇斯钦的推测。早期察哈尔万户中确实存在过称作卜尔报的蒙古部落,只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个部名消失了。
好陈察罕儿的“好陈”(qaγčin-qaučin)意为“老的”“旧的”,好陈察罕儿即“旧察罕儿”。联系到察哈尔所属的鄂托克有浩齐特( Qaγučid- Qaučid,亦有老、旧之意),和田清推测“好陈”或许和后来的浩齐特有关,浩齐特或者是由“好陈”这个词转化来的。这是非常可能的。《王公表传》说:“元太祖十六世孙图噜博罗特再传至库登汗,号其部曰浩齐特”。库登汗是达延汗的曾孙达赉逊。其实浩齐特早在达赉逊库登汗之前的达延汗分封诸子时即出现了,《蒙古源流》就说达延汗命其子阿尔博罗特(Arbolod)统率察哈尔之浩齐特。阿尔博罗特一名在《俺答汗传》中作Nal Boγura,在《大黄册》中作 Narboγura,在《北虏世系》中写作“那力不赖”。阿尔博罗特(那力不赖)有四子:失喇台吉(šira tayiǰi)、那出台吉 Naču tayiǰi)、不克台吉(Böke tayiǰi)、莫蓝台吉(Molon tayiǰi),其中失喇、那出的“营名”为“哈不慎”。一般来说,长子应当继承父亲的鄂托克,所以阿尔博罗特的鄂托克也应当是哈不慎。问题是在蒙文史书中找不到能与哈不慎完全相应的部名,赛瑞斯和森川哲雄都说不知此部究竟是怎样一个集团。哈不慎是明人经常提到的营名,甚至把它做为人名,像这样著名的部落,在蒙文史书中应当有所反映,因此我以为汉籍中那力不赖之子领有的“哈不慎”就是“好陈”,亦即蒙文史书中阿尔博罗特领有的“浩齐特”。当然,哈不慎(Qabučin)与好陈(Qaγučin)、浩齐特( Qaγučid,是qaγuči的复数形式 )在语音勘同上有很大的困难,但根据史料来看,将它们视为同一个,或者不那么勉强。我甚至觉得“哈不慎”有可能是“哈兀慎”(qaγučin-qaučin)的讹写。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浩齐特并非只存在于察哈尔,除了上面提到的哈不慎作为人名——部名存在于老把都的喀喇沁之外,浩齐特也还有鄂尔多斯部的一个鄂托克。
以上就《皇明九边考)等汉籍所载的早期察哈尔三营做了分析。但是察哈尔所属的营——鄂托克并不止此,到明末,汉文史料在称察哈尔为“八大营(八鄂托克)的同时,也称察哈尔为“三十六营(家)”。八和三十六都未必是确切的鄂托克数目,它不过是明人从蒙古那里听到的察哈尔鄂托克的概称而已,明人也并不完全相信这些说法,他们心目中蒙古的情况实际是“虏中酋首以百计,子姓部落以数十万计”。从蒙文史书来看,所载的察哈尔鄂托克也非常之多。蒙文史书一方面以不准确的方式记录了所谓”察哈尔八鄂托克”,如《恒河之流》( Pangγayin Urusqal)说:“八鄂托克察哈尔是,阿剌楚特(ALčud~ Alaγčud)、克什克腾(Kišigten)、敖汉(Ouqan~Auqan)、奈曼( Naiman)、塔塔儿(Tatar),此为山阳四鄂托克;乌珠穆沁 (Üǰümüčin)、浩齐特(Qaγučid)、克穆克齐特(Kemegčid~ Kemǰigüd)、喀尔喀(Qalq-a),此为[山阴〕四鄂托克”。《金轮千辐》( Altan Kürdün Mingγan Xegesütü)说:“察哈尔万户是,敖汉(Auqan)、奈曼(Naiman)、苏尼特(Sünid)、乌朱穆沁(Üǰümün~Üǰümünčin),此为山阳左[翼]四鄂托克;珠伊特 (ǰüγid)、博罗特(Borod)、阿喇克(Alaγ)、阿喇克绰忒( Alaγčiud~ Alaγčud),此为山阴右[翼]四鄂托克”。另一方面蒙文史书记录了察哈尔八鄂托克以外的许多鄂托克的名称,如《恒河之流》、《金轮千辐》、《水品珠》中有:额尔吉古特 (Ergigüd~Erkegüd)、乌萨沁(Uusačin~Lausačin)、特勒古斯(Telgegüs~Telenggüs)、锡巴郭沁(Šibaγučin)、萨尔古特(Sarγud)、土伯特(Tübed)、郎和沁( Longqočin)、锡拉兀鲁克(Šir-a Uruγ)、哈剌都鲁登(Qar-a Dürüdeng)、博尔多玛勒(Bordomal)、委兀慎(Uyiγurčin)、兀鲁特(Uruγud)、达赖明安(DaraiMingγan)、阿速特(Asud)。此外,《蒙古源流》还有呼拉巴特(Qulabad)、扎固特(ǰaγud);在《清实录》中,还有实纳明安(Šin-eMingγan)、多罗特(Dolod)。
如此众多的部名,一一详细指出它们的来源和统领它们的封建主,显然非常困难的。根据清代文献资料,以下诸部原属于察哈尔是确凿无疑的,它们是:敖汉、奈曼、克什克腾、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这些部都是“初皆服属于察哈尔”,在后金崛起,天下板荡之际,先后“以林丹汗不道”而降附后金,入清之后各部首领仍率本部游牧。所以尽管清代资料关于这些部的记载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仍然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它们的便利。察哈尔其它部落,有许多因文献不足而不知所终,不过还有一些仍可从清初的记载里找到它们消失的踪迹或后来的去向。下面试就几个比较重要的部落作一探讨。
(一)兀鲁特(Uruγud~Urud)
兀鲁特一名源于蒙元时期的兀鲁兀(《秘史》作兀鲁兀惕),在元代曾是五投下之一。在明代是早期察哈尔鄂托克,它应当是达延汗分封诸子时,其子格勒博罗特( Gerbolod)领有的鄂托克。
关于格勒博罗特领有的鄂托克,各书记载颇不一致。例如《蒙古源流》说他“统率察哈尔之敖罕、奈曼”,《金轮千辐》、《蒙古家谱》说他统领兀鲁特。对此森川哲雄在《试论察哈尔八鄂托克及其分封》中已有详细论述,结论是格勒博罗特领有的应该是兀鲁特,他的考证可以接受。
需要注意的是,史书中常常错误地把兀鲁特和另外一个部名“乌喇特”(Urad)相混淆,造成史实的混乱。大家知道,乌喇特的封建主是成吉思汗长弟合撒儿的后裔,与科尔沁诸部同祖。在《金轮千辐》中被列为科尔沁十三鄂托克的左翼鄂托克之一。《恒河之流》却说:“(达延汗)第十子格勒博罗特,其子隆台吉(Long tayǐǰi),其后裔是乌喇特的诺颜”。罗卜藏丹津《黄金史》也说:“达延汗之子兀鲁特台吉(按即指格尔博罗特)的后裔是乌喇特的隆诺颜”。而在《蒙古家谱》中与这段记载相应的地方则是“巴图孟克大衍汗(达延汗)第九子格勒博罗忒(格勒博罗特)之后,世封乌鲁特(兀鲁特)之隆诺音”。《蒙古源流》还将兀鲁特算作科尔沁的鄂托克,如“鄂罗郭特(Uruγud,即兀鲁特)巴图尔锡古苏特之子乌讷博罗特王”也被称作“科尔沁之乌讷博罗特王”。
混淆史实最严重的是《清史稿·明安传》。该传列举明安事迹说:“明安,博尔济吉特氏。其先世元裔,为蒙古科尔沁兀鲁特部贝勒。岁癸已(1593),叶赫贝勒布寨、纳林布禄纠九国之师来侵,明安与焉……寻修好于太祖。上闻明安女贤,遣使往聘,岁壬子(1612)正月,明安送女至……天命二年(1617)正月,明安来朝……七年(1622)二月壬午,明安及同部贝勒……并诸台吉等三千余户,驱其牲畜来归……顺治初,三遇恩诏,进二等伯。卒,谥忠顺”。这里将科尔沁的明安和兀鲁特明安混为一人了。《清史稿·明安传》依据的资料之一是乾隆初年成书的《八旗》通志初集;该书《明安传》就已混淆了这两个明安,只是更明确记载了兀鲁特的明安卒于顺治十一年(1654)。查《满洲实录》,1593年、1612年、1517年与清太祖努尔哈赤由战及和的明安,是科尔沁部贝勒,而1622年来降的明安,是兀鲁特贝勒,完全是两个人,科尔沁明安在天命二年(1617)朝见努尔哈赤后,“未几卒”,崇德元年(1636)其子栋果尔被封为镇国公,顺治五年(1648)栋果尔之子彰吉伦袭爵,七年“上追念其祖明安功,晋郡王爵,领扎萨克,诏世袭罔替”,彰吉伦所领即科尔沁左翼后旗。因此,在崇德元年(1636)之前已死的科尔沁部明安,绝不可能是活到顺治十一年(1654)的兀鲁特部明安。
兀鲁特明安是前述格勒博罗特(兀鲁特台吉)之子降台吉的儿子。《满文老档》载天命七年(1662)努尔哈赤召集蒙古诸贝勒,要求他们与女真贵族联姻时说;“四贝勒(皇太极)之亲家为兀鲁特(Urut)七贝勒中已故龙贝勒( Lung beile)正室之子明安(Minggan)及明安三子昂昆、班策及多尔济……此皆察哈尔贝勒,英明汗有意呼之为亲家,并谕之好生豢养其诸女等”。龙贝勒即隆台吉。所谓七贝勒亦见于《辽夷略》,该书载叉罕儿(察哈尔)的一支说:“初代五路,生七子”。五路即兀鲁特台吉,亦即格勒博罗特,隆台吉是他的七子之一,在此书中作扯劳害。“扯荣害之子四,曰民暗台吉……”,此民暗台吉当然就是明安台吉。
兀鲁特部与后金发生关系,最初是天命六年(1621),其年七月“蒙古兀鲁特国达尔汉巴图鲁贝勒属下十五户来归”。兀鲁特举部归降后金是天命七年(1622),其年二月“蒙古兀鲁特部明安、谔勒哲依图、索诺木、吹尔扎勒、达赖、密赛、拜音岱、噶尔玛、昂坤、多尔济、固禄、绰尔济奇卜塔尔、布彦岱、伊林齐、特灵、实尔呼纳克等十七贝勒,并喀尔喀等部台吉,共率所属军民三千余户并牲畜归附”。兀鲁特部归降后金的原因,与察哈尔属下敖汉、奈曼、乌不穆沁等部归降后金的原因相似,即努尔哈赤所说,“是因其君不仁,故慕我而来归也”。其具体原因,明臣王在晋据所获情报说:“初,五路(兀鲁特)头目妻子被贵英哈所占,头目负愤投炒花(蒙古内喀尔喀部首领),炒花不能养,投奴酋(努尔哈赤),奴酋用之守广宁(今辽宁北镇县),而以真夷(女真人)杂之。顷奴中闻我图恢复,遂尽迁五路投降之虏于海、盖间,而悉用真夷渡河以居守”。五路头目当指兀鲁特部明安,贵英哈即贵英恰,是林丹汗的宠臣,经常为获取赏金而与明朝谈判。正是林丹汗纵容宠臣贵英恰欺凌兀鲁特部,因而激起该部的不满,兀鲁特起初脱离察哈尔投奔内喀尔喀,依然难以立足,于是降附了后金。后金努尔哈赤在“欲取天下,必先征服蒙古”的战略下,对察哈尔属部兀鲁特的来归十分重视,所以在该部十七贝勒归降后,立即表示优待;“兀鲁特诸贝勒,晋其蒙古国汗,故慕我来归。凡此来归之诸贝勒若有罪,则与我八贝勒同等视之。死罪则免其死,遣还故地……”。并且令其诸子与兀鲁特诸贝勒共立誓言,表示诚心合作之意。努尔哈赤授明安三等总兵官,另立兀鲁特蒙古一旗。
然而以明安为首的兀鲁特贵族并不完全听从后金的约束,在归降的第二年即天命八年(1623),前述十七贝勒之一奇布塔尔竟故意射杀努尔哈赤近族孙女,被处以绞刑。此后十七贝勒中又有多人违犯后金统治者的纪律而受到惩处,如明安之子多尔济酒醉之后在皇帝面前拨出刀剑,又以不堪用者充当皇帝的猎户,被罚银百两;明安本人擅自以官牛给予属下,又私匿蒙古逃亡者,被罚银六十两。为此在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下令取消兀鲁特蒙古旗,“令随各旗贝勒行走,所属人员拨与吴讷格、鄂本兑旗下管理”。明安则录属于满洲正黄旗。乾隆九年(1744)敕撰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了以明安为首的很多“国初”降金后隶于八旗满洲的兀鲁特部人,列举了该部博尔济吉特等二十九种姓氏,在各姓氏之下略述了这些兀鲁特人归降的时间、任官,及其后裔的情况。《啸亭杂录》还特意记载侍卫府散秩大臣世袭者,有“蒙古明安贝勒后一人”,其中包括明安三世孙博清额。博清额在乾隆年间任散秩大臣、广州都统等职,曾修订罗密所著《蒙古家谱》,书中详细地记载了他的祖先达延汗之子格勒博罗特被封于兀鲁特及其子孙在清代任官的情况。
(二)阿喇克绰忒( Alaγčud)
这是明代蒙古的一个部名,又作 Alaγčiγud、 Alaγčuγud。《蒙古源流》和佚名《黄金史》、罗卜藏丹津《黄金史》都记载说,达延汗的曾祖父阿噶巴尔济济农属下有叫察罕(čaγan)的人,他来自阿喇克绰忒部;满都海彻辰哈屯在决定是否嫁给达延汗之前,曾向阿喇克绰忒部的桑该乌尔鲁克( Sanγai Ürlüg,或称萨岱多郭朗, Sadai Doγolang)征询意见。
此部名的来源,应即拉施特《史集》中的阿刺黑臣(Alaqčin)。阿刺黑臣居于昂可刺河(今安加拉河)与谦河(今叶尼塞河)汇流处以北地区,即唐代的曷刺(Ala)、遏罗支(Alach)。突厥语Ala(方言别写为Alach)意为“班驳的”、“白底黑斑的”,因此曷刺(遏罗支)亦被意译为驳马。阿剌黑臣——驳马以其所养马匹的毛色斑驳而著名。Alaqčin是由突厥语ala转为蒙古语alaq加词尾čin而来的,其复数形式是 alaqčiγud(阿剌黑赤兀惕),在《元朝秘史》中旁译作“花色的”,分别形容旄纛和绵羊。
《蒙古源流》和两《黄金史》虽载有阿喇克绰忒部名,但未说明它属于哪个万户。清初满文史料则明确指出阿喇克绰忒属于察哈尔( Cahar i Alakcot),清代蒙文史书也说阿喇克绰忒是察哈尔八鄂托克之一。现在来探讨一下它是由谁统领的部落。
达延汗的长子是图噜博罗特(Törö Bolod,《北虏世系》作铁力摆户),图噜博罗特二子,长子博迪(Budi,明译不地、卜赤等)继承了汗位,次子也密力台吉(又作纳密克、乜明)。《恒河之流》说:“阿拉克汗(博迪)之弟纳密克诺颜( Nemeg- Namiγ noyan)统领敖汉、奈曼、阿喇克齐特(Alaγčid)。其子贝玛台吉(Buyima tayiǰi),其二子秃昌都喇儿诺颜( Tučang durγal noyan)、额参卫征诺颜(Esen Uyi ǰong noyan)。都喇儿诺颜之子岱青杜楞(Dayi čing Düreng)……额参卫征诺颜之子衮钦达尔罕王( Günčin Darqan wang,相当于《王公表传》中额参卫征之子衮楚克)……这些是敖汉、奈曼的诺颜”。《恒河之流》所载贝玛台吉的世系虽然与《王公表传》稍有不同,但所说贝玛的子孙统领敖汉、奈曼是与《表传》一致的,《辽夷略》的记载也是如此。
纳密克之子贝玛的子孙统领敖汉、奈曼,那么阿喇克齐特(阿喇克绰忒)由谁统领呢?《北虏世系》说也密力台吉有二子,次子卑麻台吉(贝玛),长子挨大笔失台吉,我想挨大笔失台吉及其子孙就应当是阿喇克绰忒的统治者。挨大笔失又作阿牙台皮、云爱塔必,《皇明世法录》也说阿牙台皮与卜以麻(卑麻、贝玛)是兄弟。《登坛必究》载察哈尔世系说“我力命那言二子,长子不一骂台吉,次子哈喇处台吉”。我力命相当于也密力或乜明,不一骂即卑麻或贝玛,哈喇处则相当于挨大笔失。《北虏纪略》载《虏酋名目》也提到背马台吉《卑麻、贝玛》和阿喇处台吉。哈喇处台吉即阿喇处台吉,哈、阿之别是由于蒙语a,可以读作ha,词首元音前常常增加辅音h的缘故。明代蒙古经常以部落名称作为人名,所以挨大笔失又称阿喇处这一现象,表明挨大笔失统领的是阿喇处部——阿喇克绰忒部。
《北虏世系》载挨大笔失生有一子那木大黄台吉,《辽夷略》载叆塔必生有十子,其中长子脑毛大黄台吉、末子拱兔为强。那木大黄台吉即脑毛大黄台吉。《武备志》说“擦汗儿达子小部落,山前辽东地方宁远、广宁边外青山住牧,离边一百余里。长子奴木大黄台吉”。擦汗儿即察哈尔,奴木大也就是那木大、脑毛大。所谓山前擦汗儿达子小部落是相对于林丹汗所领的山后擦汗儿达子大部落而言的,亦即《清实录》所说的“南察哈尔与北阿禄察哈尔林丹汗”,山前、山后以辽西的松岭山脉为界,奴木大黄台吉及其弟拱兔台吉的驻地在山南的大小凌河流域,也就是说,阿喇克绰忒部就在这一带。
脑毛大(那木大、奴木大)在《蒙古源流》中被译作阿穆岱( Amudai),其正确的译法应当是纳穆岱(Namudai)。他是著名的首领,在图们汗(明译土蛮,1558-1592年在位)时期,曾被任命为汗廷的五执政之一,又在丁亥年(万历十五年,1587)代表察哈尔赴土默特拜谒三世达赖喇嘛。脑毛大的孙子桑河儿寨与林丹汗各娶叶赫首领金台失的两个孙女,在明人眼里,脑毛大及其弟拱兔、林丹汗被视为察哈尔部的三大酋。万历年间(1573—1620),脑毛大一方面向明朝索取市赏,一方面不断地和明朝发生边界战争,到天启二年(1622),明辽东经略王在晋谈到蒙古形势说:“西虏之近广宁者为虎墩兔(按即林丹呼图克图汗)。虎,虏中之王称憨者也,而昏于酒色,无远志。其叔脑毛大专权得众,又老而不能自强”。五年后的天启七年和崇祯元年(1627—1628)之交,林丹汗以强力压服属下诸部不成,又面临后金高压,便向西迁移,于是察哈尔的敖汉、奈曼,内喀尔喀的巴林、札鲁特等部纷纷降附后金,阿喇克绰忒也开始有零散人马来到后金,如“(天命十一年,1626)十一月戊寅,察哈尔阿喇克绰忒部落贝勒图尔济率人口百户来归”,“(天聪元年,1627)八月壬子。是日,察哈尔国阿喇克绰忒部巴尔巴图鲁、诺门达赉、吹尔扎木苏三贝勒率男子十五名,妇人十四口,幼小十口,马四十五匹来归”,“(天聪元年)十二月甲午朔察哈尔国阿喇克绰忒部落贝勒图尔济伊尔登携妻子人民来降”。
然而阿喇克绰忒的大部人马,仍然对后金桀骜不驯,因而遭到后金的征讨。《满文老档》载:(天聪二年,1628)二月初二日,满洲国天聪汗遣往喀喇沁大臣,为察哈尔多罗特(Dolot)部两次截杀。满洲国天聪汗遂亲率偏师,前往征察哈尔蒙古所属阿拉克绰特部(Cahar iMonggo Alakct gurun)。
二月初八日申时起行……十五日……前行诸贝勒,擒人讯之,言色楞青色图鲁,并其部众,俱在敖木伦(Oo Muren,按即大凌河上游)地方等语……汗与诸贝勒,率军驰击之,多罗特部多尔济哈坦巴图鲁(Dorǰi Hatan Baturu)负伤遁走,尽获其妻子,杀其台吉古鲁(Guru)。俘获一万一千二百人,以蒙古、汉人男丁一千四百名,编为民户,余俱为奴”。
参与进攻阿喇克绰忒部的,还有已降附后金的蒙古奈曼部的出期巴图鲁,他因为斩杀阿喇克绰忒台吉噶尔图,俘获七百人,被皇太极授予达尔汉之号。就当时的蒙古部落而言,阿喇克绰忒仅被俘的人数就能够达到一万一千余名之多,堪称人众势强的大部。然而经过这样的打击,阿喇克绰忒部终于土崩瓦解,除伤亡遁逃者之外,俘虏中少量被编为民户,多数沧为奴属。其原驻地很快被察哈尔的另一支势力——顾特塔布囊(Gutei tabunang)占据,由于顾特塔布囊截杀归降后金的蒙古人,也很快在后金的征讨下灭亡了。
需要指出的是,按照《满文老档》的上述记载,天聪汗是因为多罗特部截杀使者,所以征讨阿喇克绰忒部,而在战斗中遁逃和被杀的,又是多罗特的多尔济哈坦巴图鲁和古鲁。似乎多罗特和阿喇克绰忒是同一个部落。多罗特为察哈尔所属,除《满文老档》之外,没有其它史料可为佐证,它与阿喇克绰忒的关系,也无从考究。在这里,我们暂且将多罗特和阿喇克绰忒视为同一个部落。
流散的阿喇克绰忒部人处境艰难。天命八年(1634)该部的巴图鲁阿拜与喀剌沁的班第卫征不得不归降后金,他们一起死于途中,其原因是“来归之人同类中互相杀夺”。这个巴图鲁阿拜可能就是《辽夷略》所载的云爱塔必(阿牙台皮、挨大笔失)之孙把兔儿阿败。天聪二年二月战斗中负伤遁逃的多尔济哈坦巴图鲁等人,跑到明朝的锦州城,为明助力。天聪八年后金和硕贝勒岳託特意差一蒙古人前往劝降,称多尔济哈谈(多尔济哈坦)等人是多罗特部的豪杰,希望他们审时度势,弃明而归。又有多罗特部的苏班代等六十余人投往明军驻守的杏山(今辽宁锦州市南)居住,崇德五年(1640)与清军联络,意欲归附。清太宗对此十分重视,立即派遣济尔哈朗、多铎等人率军一千五百前往接应。苏班代等携其家资牲畜逃出,明军随之追击,与清军遭遇,酣战一场。随后苏班代等人得到太宗的赏赐,苏班代还被授予三等甲喇章京之职。
在蒙古、后金、明朝三大势力角逐的动荡年代,曾经拥有较强力量的阿喇克绰忒部没有象许多蒙古部落那样“举部归附”后金,部众终于散亡,入清之后连这个部落的名称也消失了,只是在“散处于阿喇克绰忒等地方公吉喇特氏”、“世居阿喇克绰忒地方锡尔哈氏”这类记载中还可以看到它的残存。
(三)察哈尔所属诸部中略有踪迹可寻的部落还有一些,如实纳明安、打剌明安、阿速特等。
实纳明安(Šin-e Mingγan)由林丹汗的祖父车臣汗(即布延彻辰汗 Buyan Sečen qaγan)之弟岱青(Dayičing)领有。林丹汗即位后,尽夺其叔祖岱青部民,岱青率其妻及六子逃往科尔沁。天命十年(1625)岱青之子扎尔布(Jalbu)、色棱(Sereng)从科尔沁谒见努尔哈赤,表示归降之意金。
打剌明安( Darai Mingγan)是达延汗之子阿尔博罗特(Arbolod,即那力不赖)的儿子莫蓝台吉(Molon tayiǰi)的部名,亦即《登坛必究》中抹蓝台吉的打喇名安,在《国榷》中又作打来明喑。《满文老档》载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向八旗中的蒙古贵族颁发赏赐,受赏的人中有不少塔赖明安部(Tarai Minggan)人。由此可以推测,打剌明安在明末清初可能大部被编入八旗之中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载有隶于满洲正蓝旗的原“世居鄂嫩果尔地方达喇明安氏”的蒙古人。
阿速特(Asud)与永谢布(YöngŠiyebü)都是达延汗之子巴尔斯博罗特的儿子博迪达喇鄂特罕台吉( Bodi Dara Odqan tayiǰi)领有部落。阿速特、永谢布、喀喇沁三部统称永谢布万户。但是同一部名见于不同的万户之中,是明代蒙古常有的现象,阿速特同时也见于察哈尔万户。《恒河之流》、《金轮千辐》都说阿尔博罗将统领的部落之一是阿速特。《清实录》也说是“察哈尔阿苏特部落”,在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征察哈尔时,该部有“男子十二名,妇人三口来归”。在此之前的天聪五年(1631)得到皇太极赏赐的八旗中的蒙古贵族中也有不少阿速特部人。因此可以推测,包括察哈尔阿速特在内的蒙古各万户所属的阿速特部民,也大部被编入八旗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载有隶于满洲正红旗的原“世居西喇塔拉地方阿苏特氏”的蒙古人。
除了上述提到的察哈尔诸部之外,还有相当多的据蒙文史书所载属于察哈尔的部落,因为资料有限,不要说详细探究它们的形成和入清后的去向,即使证明它们确为察哈尔所属,目前以难以做到。但是据以上所述,至少可以证明,所谓八鄂托克察哈尔云云,或可反映察哈尔某一时期的情况,绝不可能反映察哈尔在长时期中的发展变化。
待续……
文/薄音湖
文章来源:《察哈尔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编辑/吴晓倩
审核/温都苏
摄影/刘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