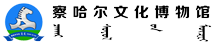编者按:明・额尔敦巴特尔,男,蒙古族,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历史学系副研究员,内蒙古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历史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研究成果:《林丹汗与蒙古佛教》(原文日文)、载日本《三康文化研究所年报》第32号、《蒙古林丹汗“蒙古文金字甘珠尔经”的若干问题》(中文),《察哈尔万户八大鄂托克之一“乃蛮”及其宗教》(蒙古文)、《关于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若干问题》(中文)等学术论文。
数十年来,他始终在蒙古历史文化教学科研岗位上勤奋努力、耕耘不辍,为蒙古宗教史、察哈尔史、成吉思汗祭祀史研究倾注心血,为国家培养人才竭诚尽力。多次受邀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论坛,接受国内外各级媒体的采访报道,在传承弘扬察哈尔历史文化,抢救保护珍贵文化遗产,繁荣发展民族文化事业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受到了各级领导高度赞誉和国内外学者的爱戴。
社科普及
一、前言
1206年,成吉思汗登基并创立了大蒙古国。1227年成吉思汗逝世之后,“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每个斡耳朵都为死者举哀一天。讣闻传到远近地区时,后妃,诸王[奔驰]多日从四面八方来到那里举哀死者。由于某些部落离那里很远,大约过去三个月后,他们还陆续来到那里举哀死者”。从此,成吉思汗被作为“守护神” 来祭奠。
笔者认为,成吉思汗祭祀活动,窝阔台汗在位时期(1229-1241) 就已经开始,到忽必烈汗时期实施成吉思汗的“四季祭祀”并制度化,成吉思汗祭祀成为“蒙古精神文化史的三大体系”之一。16世纪中期以后,成吉思汗祭祀文化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成吉思汗逐渐被“双重神化”。
有关成吉思汗祭祀,存在一部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竹笔抄本。这部蒙古文《圣成吉汗祭祀经》,是由道荣嘎先生于1958年在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哈撒尔祭殿斡耳朵之洞穴中发现。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竹笔抄本是在纸面表里双面书写的贝叶经式文献,包括扉页和不完整的页数在内,共有99页面,除“残片”以外,每页纸面上用竹笔书写有16行到18行的蒙古文,其大小为28×10cm。
首先,1988年,N.胡尔查利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所藏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史料发表了论文,认为16世纪中期以后曾经存在以察哈尔为中心的成吉思汗祭祀活动。其次,意大利学者Elisabetta Chiodo于1989年发表了有关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前半部分的部分英译及注释。两年后,她又发表了部分英译及注释。Elisabetta Chiodo的研究是迄今为止对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较为详细的研究。她认为,有可能在鄂尔多斯以外的地区也存在过成吉思汗的祭祀场所。再次,1998年,道荣嘎以《成吉思汗祭祀经——蒙古古籍汇集》的书名出版了《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影印本及其注释,除了《圣成吉思汗祭祀经》外,书中还收集了《成吉思汗“黄金史纲”传记》和在成吉思汗祭祀上歌唱的《十二首天歌》以及题为《大蒙古》的天歌歌谱等内容。最后,那顺乌力吉于2002年和2008年分别发表了论文,认为《圣成吉思汗祭祀经》中所记载的内容是“在察哈尔举行的蒙古汗廷天地祭祀规定”,而且“该规定无疑是在1368-1438年之间写就的”。
另外,笔者于2008年在国际蒙古学杂志上曾发表不成熟的英文论文,介绍了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本论文是对其进行增删修改而成的,并通过史料的重新分析,就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成立时期、内容特点及其重要历史意义等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
二、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成书时期及若干重要问题
简要地说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内容,它就犹如《白史》中提及的、为祭奠成吉思汗而举行的“四季祭祀”。所谓“四季祭祀”是指蒙古人为祭奠成吉思汗而举行的季节性的祭祀,即春季祭祀、夏季祭祀、秋季祭祀和冬季祭祀。由于《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抄本的后半部分(27b-49a) 的损坏严重,几乎不能判读,因此在此主要根据《祭祀经》前半部分(1a-27a)中关于夏季祭祀和秋季祭祀的记述加以分析。
(一)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成书时期
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中没有写明作者和成书年代。关于《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作者,目前只能说“作者不明”。至于何时成书的问题,通过分析《祭祀经》的内容,可以大致特定其成书时期。
第一,在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中多次出现“八鄂托克·察哈尔万户” 这一固定词句。
察哈尔是15-17世纪蒙古大汗直属万户的名称,也是蒙古本部“六万户”的左翼三万户之首。据《黄金史纲》记载,蒙古“六万户”的提法,在15世纪后期满都古里汗时期就已被惯用。而“六万户”之一的察哈尔万户的名称,早在15世纪中期也先汗时期就见诸蒙古史籍,16世纪中期有了汉文记载,17世纪起有了满文记载。另据《黄金史纲》记载,察哈尔主要鄂托克的名称,比如,克什克腾、浩齐特、克木齐古特、阿拉克楚特和乌珠穆沁等都出现在达延汗时代。据《蒙古源流》记载,乃蛮部人早在达延汗的祖父哈尔古楚克时代就作为哈尔古楚克的仆从已经出现。这表明,乃蛮人至少从这一时期起就已经成为察哈尔的成员。另外,《蒙古源流》也记载着苏尼特、察哈尔·忽拉巴特·鄂托克、克木齐古特、克什克腾、敖汉、乃蛮以及浩齐特等察哈尔诸鄂托克。那么,察哈尔是何时组成8个鄂托克的呢? 首先“八鄂托克·察哈尔”"这种说法早在达延汗时代就已成为惯用名称。换言之,这一说法在达延汗去世的1517年之前就已成为惯用名称。其次,据《黄金史纲》记载,达延汗去世后,博迪阿拉克曾迫使巴尔斯博罗特让位于他。但是,巴尔斯博罗特·赛音阿拉克即位后,实际上“未及治理政事”,即死于1519年(兔年)。随后,博迪阿拉克在1521年即位,成为博迪汗。到博迪汗即位时,察哈尔诸鄂托克的数字已经超过了8个。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察哈尔在16世纪初期之前已经组成了“八鄂托克”。
第二,失宝嗔,又作“失宝赤”在《圣成吉思汗祭祀经》中作为察哈尔的属部,以“失宝赤千户”的形式出现。《蒙古源流》第69v中提到鄂尔多斯万户右翼部落中有失宝嗔一部,是衮必里克“济农”次子伯桑豁儿的属部。而明代汉籍则记载,永谢卜部内也有“失宝嗔”一营。至于“失宝赤千户所”,是在1371年(明洪武四年)设立的。该地在元东胜州地区,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一带。另外,《圣成吉思汗祭祀经》中出现的塔塔儿,恐怕是指察罕·塔塔儿。据《蒙古源流》记载,巴颜答喇生于壬申年( 1512)并统治察哈尔的察罕·塔塔儿鄂托克。至于克木齐古特,早在 15世纪莫兰汗时代就已出现。
第三,所谓察哈尔万户“东迁”是于1547年博迪阿拉克汗去世之后,在打来孙库登汗时期发生的。而且,从《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核心内容和发现地点等来看,《圣成吉思汗祭祀经》 反映16世纪40年代末察哈尔万户“东迁”"之前的成吉思汗祭祀古时状况。
第四,在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中也出现了一些“祭祀司仪者”名称,比如“Manglai”(祭祀“带头人”或“总管”)、“Tabiγ Tabiγǎi”(供养人)、“Sir-biǎin”(持神符者)以及“cargiǎin”(敲响板者)等等。这些名称在1330年成书、16世纪后期经过修改的《白史》中几乎也曾出现过。
第五,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中,未提及“jinung”(济农)这一官职。其实“济农”是从“晋王”音变而来的,它与镇守蒙古高原本土的元世祖嫡孙甘麻辣的“晋王”一职有关。元代,皇帝坐镇都城大都,晋王镇守蒙古本土,守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而且在“1438年以后,即也先统治时期,在蒙古出现了可汗与济农分管左右两翼的政治制度并开始出现了六万户。察哈尔万户作为六万户之一,形成于这一时期”。但是,在达延汗统一蒙古本部六万户之前,虽然有“济农”这一称号,然而于1510年之前的历任“济农”,是否直接掌管成吉思汗的“八白帐”并不明朗。因为,达延汗通过1510年的“达兰·特利衮之战”征服了蒙古右翼万户之后才正式任命巴尔斯博罗特·赛音阿拉克为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帐”的右翼三万户“济农”的。
综上,笔者认为,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抄本,成书于16世纪初期,即蒙古博迪阿拉克汗即位的1521之前。
(二) 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若干重要问题
首先,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重要内容是关于蒙古可汗自身怎样举行成吉思汗祭祀中的诸礼仪的详细描述。换言之,这部《圣成吉思汗祭祀经》是关于蒙古时任可汗亲自出席成吉思汗祭祀仪式,并规定可汗怎样亲自完成仪式过程中诸多礼节的礼仪指南书。以史料为例:
(汉译)当可汗驾到时,灵帐(毡帐) 的诺颜骑马迎接,(从可汗一行) 领取明灯的神酒(《祭祀经》,2b) 。
这就是说,可汗一行为祭奠成吉思汗而带来了“神酒”,然后,可汗将神酒怎样呢?
(汉译)将那神酒斟入献祭用的酒杯(碗) 里,再将(斟好的) 神酒献在内灵帐(正殿)左侧前方,必须在马奶之前供乳羊羔。当供整羊时,灵帐的诺颜必须将布巾和成双的酒杯,让(祭祀) 带头人拿着。供好整羊,灵帐的诺颜禀报可汗后,可汗应跪地礼拜。从白马群的马奶中斟入献祭用的碗里,由“灵帐诺颜”将它端着。然后向天献酒时,可汗应在座上礼拜,祝词者献上神酒,吟咏祝词。可汗和“灵帐诺颜”二人向前迈进,将整羊肉供在灵帐(祭殿)的灵前。供整羊时,带头人必须将斟满马奶的金杯和布巾,一起拿着。带头人再将成双的金杯交给助理人员。可汗必须将金杯酒供在灵帐(祭殿) 内的金桌上(《祭祀经》,4b-5b)。
可见,可汗一行为祭奠成吉思汗而带来的神酒,和整羊一起被供在成吉思汗灵帐的金桌上,而且可汗亲自率先举行礼拜和各种仪式。
那祭祀仪式如何继续呢?
(汉译)接着,成双的酒杯里斟入一半神酒,举起酒杯举行礼拜。当斟满酒杯唱诵《大蒙古》这一歌曲时,可汗将成双的酒杯拿去举起三回后,供在主灵帐(正殿) 内的金桌上,后退跪着举行礼拜(《祭祀经》,11b-12a)。
可见,在察哈尔万户举行的成吉思汗祭祀仪式中曾唱诵《大蒙古》这一赞歌。有趣的是,20世纪在鄂尔多斯举行的成吉思汗祭祀仪式中人们也唱诵《大蒙古》这一赞歌。而且,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也收录了北京故宫所藏《大蒙古》这一歌曲的歌谱。
其次,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中登场的祭祀仪式司仪是称作“灵帐诺颜”(gerün noyan)的主持者,而称作“济农”的主持者却一概不出现。
《圣成吉思汗祭祀经》所描述的成吉思汗祭祀仪式中,称作“灵帐诺颜”的人员才是祭祀仪式的指导者,据悉,成吉思汗“八白帐”,曾有过40名“灵帐诺颜”。后来有了“八大官吏”其首领是“济农”。在鄂尔多斯举行的成吉思汗祭祀中,“济农”始终率先举行礼拜。
值得关注的史实是,达延汗征服蒙古右翼三万户之前,曾经委派次子兀鲁斯博罗特(又名:阿巴海)为右翼三万户的“济农”。然而,兀鲁斯博罗特(阿巴海)到达右翼之后,准备在圣主神位之前即“济农”位的时候却被右翼贵族杀害。因此,如上所言及,达延汗于1510年经过“达兰·特利衮之战”征服了蒙古右翼三万户之后,再次任命三子巴尔斯博罗特· 赛音阿拉克为蒙古右翼三万户的统帅“济农”。从此,巴尔斯博罗特·赛音阿拉克成为达延汗统一蒙古后的第一任“济农”但是,《圣成吉思汗祭祀经》所描述的成吉思汗祭祀仪式中,理应出现的“济农”却一概不登场。究其原因,至少有两种可能: 其一,《圣成吉思汗祭祀经》所描述的成吉思汗祭祀根本不在鄂尔多斯,因此“济农”未登场;其二,《圣成吉思汗祭祀经》所描述的成吉思汗祭祀或许反映了巴尔斯博罗特“济农”被正式任命之前的祭祀状况, 因此祭祀活动不是由“济农”主持,而是由称作“灵帐诺颜”的司仪主持。
最后,据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所述, 成吉思汗祭祀仪式所用供品,主要由察哈尔的诸鄂托克贡献。原文如此记载:
(汉译)立夏祭祀在仲夏5月15日举行。“八鄂托克·察哈尔万户”,按季节提供马和羊。乳羊羔由斡耳朵的“白群”放牧人提供。乃蛮鄂托克纳贡20 (樽) 酒( 即神酒) 。两“古雅”鄂托克各纳贡 15(樽) 酒。其区别为其他鄂托克同样各纳贡 20 (樽) 酒,但“失宝赤千户”要纳贡40(樽)酒。所谓两“古雅”鄂托克指的是,右翼塔塔儿纳贡 15(樽) 酒,左翼克木齐古特[一字不明]纳贡15(樽) 酒。共计有210(樽) 酒(《祭祀经》,1a-2b)。
以上史料中,虽然使用着“八鄂托克·察哈尔万户”这一惯称,但从后面的表述来看,蒙古察哈尔万户诸鄂托克之数已不止8个。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妨用数学公式计算一下“其他鄂托克”酒的总数和其他鄂托克的具体数字。根据史料表述,乃蛮鄂托克20 (樽)酒,“失宝赤千户”40樽酒,两“古雅”鄂托克即右翼塔塔尔和左翼克木齐古特各15樽酒,共计210樽酒。那么其他鄂托克酒的总数是多少呢? 我们把这个未知数用X来表示的话,就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计算。
20+40+(15×2)+X=210
90+X=210
X=210-90
X=120(其他鄂托克酒的总数)
因为史料中说“其他鄂托克同样各纳贡20樽酒”,所以,其他鄂托克之数为:120(其他鄂托克酒的总数)÷20=6(其他鄂托克数)。这样,加上史料中已出现的有具体名称的几个鄂托克,察哈尔诸鄂托克的数已超出了8个。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圣成吉思汗祭祀经》所描述的成吉思汗祭祀并没有将祭祀活动仅仅限定在当时蒙古中央部落察哈尔万户。《圣成吉思汗祭祀经》同时也记载着,祭祀仪式上的可汗“大恩赐”(yeke tǖgegel)的范围,涉及当时蒙古六万户等。
(汉译)接着举行“大恩赐”(yeke tǖgegel),首先赐赏(祭祀)带头人,[中略]然后对五色兀鲁斯、六万户和“八鄂托克·察哈尔”等他们所有人,按照兄弟之别给予赐赏(《祭祀经》,4b)。
可见,蒙古可汗“大恩赐”范围,涉及“五色兀鲁斯”和“六万户”等。《祭祀经》中所说“六万户”,无疑是指蒙古本部六万户即左翼察哈尔、喀尔喀、兀良罕、右翼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卜等六万户。
三、小结
通过以上论述,首先,笔者认为,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是16世纪初期,即1521年蒙古博迪阿拉克汗即位之前成书的关于成吉思汗祭祀的重要祭典文献。
其次,这部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存在证明,在蒙古左翼察哈尔万户曾经举行成吉思汗祭祀。但是,从祭祀仪式上可汗“大恩赐”的范围看,祭祀活动涉及“五色兀鲁斯”和蒙古六万户即察哈尔、喀尔喀、兀良罕、右翼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卜等。可见,当时的成吉思汗祭祀至少是蒙古本部六万户的祭祀活动。
再次,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详细记述了蒙古民族成吉思汗祭祀的古时状况。可以说,这部《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重要性在于,它使人们获悉了成吉思汗祭祀的16世纪初期之前的早期状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圣成吉思汗祭祀经》是仅次于“至顺元年(1330) ”成书的《白史》的、极其重要的蒙古文祭典文献。
最后,这部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重要性还在于,它记录了蒙古可汗亲自率先参加成吉思汗祭祀的详细状况。换言之,这部《圣成吉思汗祭祀经》是关于时任蒙古可汗亲自出席成吉思汗祭祀仪式,并规定可汗怎样亲自完成仪式过程中诸多礼节的礼仪指南书。蒙古史书中经常记述,当举行即位仪式等重要仪式时,蒙古可汗自身势必在成吉思汗“八白帐”(又作八百宫) 的灵前举行礼拜的事实。而这部《圣成吉思汗祭祀经》中极其详细地描述了蒙古可汗自始至终在成吉思汗祭祀仪式中亲自完成诸多礼仪的细节,这是极其重要的。
文/明・额尔敦巴特尔
文章来源:2017“察哈尔文化·乌兰察布论坛”论文集
编辑/吴晓倩
审核/温都苏
摄影/刘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