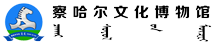编者按:庆歌乐,蒙古族,中共党员,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曾担任民族音乐学系副主任。现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员、内蒙古科尔沁民歌协会理事、内蒙古自治区音乐家协会键盘乐学会会员、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会会员。
发表学术论文15篇,其中国家级核心刊物4篇,教学改革与民族音乐研究多篇(蒙、汉文);主持省部级艺术专项课题1项,校级课题4项,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多项;参与编写的教材《蒙古族风格音乐创作》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全区第七届民族教育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多年来,致力于民族音乐学、蒙古传统音乐等方面研究,积极参与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各项
活动,并在察哈尔文化“乌兰哈达论坛”等重要学术平台上发表了价值较高的论文,为察哈尔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社科普及
二、《阿斯尔》是察哈尔文化重构的产物
内蒙古音乐界对于《阿斯尔》乐曲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近些年来,由于内蒙古地区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以及地方政府致力于打造文化品牌,《阿斯尔》乐曲的研究与表演方面,出现有持续走高的趋势。研究者分布较为广泛,从内蒙古首府著名的理论家、教授、演奏家,直到地方高校教师以及研究生,还有地方表演团体的编创与演奏人员,都在关注《阿斯尔》乐曲。
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一般规律: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对《阿斯尔》乐曲的认识也是如此。例如,有关《阿斯尔》乐曲的产生年代问题,成为内蒙古音乐理论界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然而,由于文字记载的缺乏或简略,学术史的短暂,比较音乐学开展的相对滞后,对《阿斯尔》研究带来了相当的困难。如前所述,蒙古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转型推动了《阿斯尔》的产生。从音乐方面来说,《阿斯尔》则是察哈尔蒙古部落文化重构的产物。笔者认为,无论古今中外,各民族的器乐曲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无疑受到本民族民歌的深刻影响,反之,民歌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也会受到器乐的影响,二者相互影响,共同推动民族音乐的发展。笔者采访锡林郭勒盟镶黄旗乌兰牧骑原队长伊拉拉图,他说:“有歌词的《阿斯尔》和没有歌词的纯器乐化的《阿斯尔》,这两种形式好像商定好一样,前者在蒙古国有关于《阿斯尔》诗歌的遗存;后者以民间器乐曲形式出现,主要在内蒙古地区流传。”镶黄旗乌兰牧骑艾日布先生、内蒙古艺术学院艺术研究所所长乌力吉巴雅尔先生,也持有此类的观点。认为古代蒙古宫廷音乐中,好几首宴歌含有“阿斯尔”之类赞美性词汇,说明《阿斯尔》乐曲与《阿斯尔》宫廷歌曲有内在联系。
《阿斯尔》既然是文化重构的产物,歌曲产生的年代和乐曲产生的年代,并不是同步的。总的来说,歌曲产生的年代要早于乐曲。例如,短调歌曲《阿苏如》,三句乐段体结构,宫调式,保留着元代宫廷歌曲的遗风。其歌词与《笳吹乐章》中的特定词汇相似,极有可能是北元时期的宫廷歌曲。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拿这个例子来证明,《阿斯尔》乐曲也是北元时代的宫廷歌曲呢?当然不可以。民间流传的古老民歌中,有的是蒙古汗国时期的产物,还有的是元代的产物。至于明清时期的民歌,数量更多些。科尔沁地区的萨满歌曲中,甚至还有原始音乐曲调。有的萨满教歌舞曲调,竟然与匈牙利民歌是同宗曲调。所谓重构,就是按照新时代的要求,重新整合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文化。《阿斯尔》的曲目中,既有元代至北元时期的宫廷歌曲,也有满族、汉族都统带来的外来音乐文化,尤其是在器乐方面,这一现象更加明显。因此,蒙古族固有的宫廷歌曲,与新型的器乐曲相结合,这并不自相矛盾,恰好是文化重构的必然现象。
然而,从《阿斯尔》音乐的时代风格方面来看,歌曲和器乐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前面说过,歌曲产生的年代相对古老,民族风格更加浓郁。反之,器乐套曲产生的年代则比歌曲晚,民族风格也不如歌曲鲜明。其实,文化内涵、音乐审美方面,《阿斯尔》存在着内在矛盾。从内蒙古地区来看,察哈尔地区的管理体制,确实是特例,存在种种矛盾。《阿斯尔》音乐中隐含的矛盾,恰恰是察哈尔社会深层矛盾的曲折反映。
《阿斯尔》既然是文化重构的产物,音乐资源自然也是重构而成的。其特点是历史跨度较长,包括元朝——北元——清朝以来察哈尔地区的歌曲资源。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察哈尔蒙古人在创造《阿斯尔》宴乐时,吸收了流传于民间的元明时期歌曲,其中包括一些宫廷歌曲。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阿斯尔》乐曲产生于康熙年间,从而否认歌曲中包含元代——北元时期的蒙古宫廷歌曲。反之,我们也不能因为《阿斯尔》歌曲中包含蒙古宫廷歌曲,反过来证明《阿斯尔》乐曲也都产生于元代——北元时期。
阿斯尔的产生年代目前也有不同的说法。内蒙古有部分学者认为,《阿斯尔》乐曲产生于元代。现将其所持理由介绍如下:《阿斯尔》曲目分为两大类:一是有歌词的《阿斯尔》歌曲,另一类则是无歌词的《阿斯尔》,属于纯器乐曲。认为《阿斯尔》乐曲是从古代宫廷宴歌演变而来的。当地老一辈民间艺人们说:阿斯尔最早是有歌词的,后来歌词失传了,变成多种变体形式的阿斯尔。人们之所以把在宫殿中演奏的器乐曲称做“阿斯林·温都尔”或“阿斯尔”,是因为蒙古人把古代蒙古可汗等贵族们居住的府邸,称做“斡耳朵·哈日希”(宫殿)或“阿斯尔·塔克塔”(楼阁)。因此,有的学者通过对元朝宫廷宴歌《皇家白马群之歌》(传说)、清朝宫廷蒙古乐曲《笳吹乐章》中的《牧马歌》、器乐曲《阿斯尔》三者间关系的考证,试图说明《阿斯尔》的演变过程。通过对宴歌歌词内容的比较分析,以及对《阿斯尔》的音调特征,与宴歌音调特征相联系,进一步推论《阿斯尔》的产生年代,至少可以追溯至元朝。
虽然“阿斯尔”这种传统的合奏形式与元代的宫廷音乐、北元时期林丹汗宫廷音乐中的蒙古宫廷器乐合奏类似,但在关于蒙古族为数不多的历史文献,如《蒙古秘史》、《元史·礼乐志》、《蒙古风俗鉴》、北元宫廷音乐《番部合奏》与《笳吹乐章》以及清朝《五体清文鉴》、《律吕正义后编》等官修正史、文献以及民俗文献资料中,至今人们尚未找到与《阿斯尔》完全一致的器乐曲名称。近些年,在学术界和表演界,对于它的音乐属性的定位讲得最多的是“宫廷音乐”。毋庸置疑,在历史上看察哈尔地区宫廷音乐非常发达。
探讨宫廷音乐属性的定位问题:
首先,无论是器乐还是声乐,受蒙古宫廷音乐风格影响较深。长期以来,上都一直是元朝的政治文化中心——首都。上都是蒙古宫廷音乐的中心之一,宫廷音乐十分发达,诸如潮尔合唱、赞歌、酒歌等对民间音乐产生了深刻影响。那里曾产生过许多著名的蒙古族作曲家,诸如硕德闾,他所创作的器乐曲《白翎雀》,以及琵琶名曲《海青拿天鹅》之类。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华,元世祖就是在上都接见他,并举行盛大宫廷宴会,表演文艺节目款待之。直至蒙古的末代国君林丹汗,那里的宫廷音乐素来发达。不难想象,《阿斯尔》音乐产生于这片土地,与宫廷音乐的产生环境、功能用途方面很相似,故《阿斯尔》有着古老、坚实的历史文化根基与鲜明的地域特色,可以推测遗留宫廷音乐的可能性,必然受到蒙古宫廷音乐的间接影响。
其次,上都又是蒙古族古典文人音乐十分发达的地方。因为除却宫廷音乐家,上都也是蒙古族文人雅士云集之所,他们当中熟谙音律,弹琴鼓筝,精通作曲者大有人在。这些人所创作的乐曲,并不属于宫廷音乐范畴,在社会上广为流行。但在传播过程中,不排除传入宫廷中去。
第三,元上都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都市,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除了蒙古居民之外,那里还生活着大批汉族、色目、西域、中亚,乃至来自欧洲的文臣武将,包括乐工歌伎之类艺术人才。他们在学习蒙古音乐的同时,也必然把自己民族或国家的音乐——包括乐器、乐曲带到上都,对蒙古族音乐产生一定影响。
正确理解和处理好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蒙古族音乐与其他民族音乐的关系,历来是蒙古族音乐史上的重要课题。确实如此,我们对《阿斯尔》进行纵向和横向的研究,都会感到此问题的存在。《阿斯尔》作为蒙古族古代宴乐,与宫廷音乐必然有一定的联系,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必然走向绝对化。相反,把《阿斯尔》的宫廷音乐属性与元代蒙古宫廷音乐的遗留直接等同起来,也缺乏足够的历史根据,需要谨慎。
音乐文化基因的整合传承在古代音乐与当代音乐的关系中十分重要,我们常常采取逆向思维的考察方式去回溯历史,还原过去。例如,福建省的“潮州锣鼓”、高甲戏之类,尚保留着唐代音乐的某些特点,被人们称之为“活化石”。同样,内蒙古河套地区的“爬山调”,陕北地区的“信天游”,其上下句的民歌形式,与匈奴人的《祁连山歌》如出一辙,具有文化上的渊源关系。然而,我们毕竟不会认为,“潮州锣鼓”即等同于唐代音乐,“信天游”就是匈奴民歌吧。
蒙古建筑中同样存在着重建重构的情况,如蒙古国的额尔德尼昭(光显寺),1586年兴建于哈拉和林城旧址。建筑材料中的砖石部分,主要来自于蒙古汗国时期的哈拉和林建筑群。历史上的额尔德尼昭,曾两次被毁两次重建。木料得以更新之外,砖石材料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又如,我国河北省长城沿线的农村,有些建筑利用了大量的长城砖石。国家修复长城时,农民将砖石捐献了出来。可以肯定,人们看到额尔德尼昭庙宇中有来自哈拉和林城建筑材料,不会说该寺庙是蒙古汗国时期的产物。
从文化渊源与美学内涵上说,《阿斯尔》确实与蒙古族宫廷音乐、古典音乐具有一定的联系。但这种联系更多的表现为文化基因上的、美学内涵上的继承,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
三、当代“阿斯尔”舞台艺术的话题
对于《阿斯尔》来说,无论出于表演的需求,还是研究的初衷,客观的复原态度和严谨的历史考证是非常必要的。
现今舞台上多见的是集潮尔宴歌、呼麦、歌舞等艺术形式与阿斯尔乐队的整合,成为集歌、舞、器乐等艺术为一体的综合性表演,彰显出舞台艺术强大的功能性。毋庸置疑,对于现代化舞台的表现与观众的认可程度是有目共睹的。但笔者认为,对于民间器乐曲《阿斯尔》的多种表演形式,如独奏、重奏与合奏、挖掘与创新方面还不够深入,建议集合作曲家、音乐学家、音乐史学家等参与下,共同创作出既不丢弃传统特色,具备不同形式,又赏心悦目的器乐化《阿斯尔》作品。人类学家认为,文本不一定非得是写就的,用文本可以指代被“阅读”、阐释和赋予意义的任何东西。这一术语可能指代一部电影、一个形象或一个事件。笔者作为观众从两次《阿斯尔》演出的事件、形象和活动中收获到自己认知的意义和情感。笔者作为“读者”在观看演出“节目单文本”和“演出的文本”之后,在赞叹之余,也感到有一些问题值得与学界探讨:
(一)《阿斯尔》从民间器乐曲形式发展到宫廷歌舞乐的综合形式;
随着时代的需求,大众对于传统音乐的重新认识,对于舞台艺术效果的认同以及音乐审美能力的提高等因素,传统器乐合奏的传统表演形式也随之发生着变化,原为民间器乐曲的“阿斯尔”现已发展成为集歌、舞、乐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并通过专业舞台艺术的传播加之市场的运作,在当代观众面前展现着一种新的表演形式。
(二)集欢悦的宴乐(宴飨乐)功能与严肃、恢弘的雅乐功能为一体;
阿斯尔在当代的传播与舞台化创新使我们看到了阿斯尔的另一面,即经过重构之后的阿斯尔,是以依托锡林郭勒盟当地的民间音乐资源,通过对器乐曲阿斯尔品牌的树立,整合利用蒙古族不同音乐体裁形式和不同的题材表现内容,并不是借鉴西方的音乐形式与表现形式,从而使其表演形式、内涵方面无不渗透着蒙古族的种种文化元素。这与原生性的阿斯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三)《阿斯尔》的蒙古语含义的内涵与外延的扩大。
《阿斯尔》在节目中已经不是一个音乐体裁的名称,而是整个音乐的代名词,这使得观众们眼前为之一亮。“阿斯尔”——“阿苏茹”,蒙古语语义为崇高、伟大之意,作为蒙古语副词或形容词,有非常、特别的含义。原本理论界的语言学成就在舞台艺术表演的语境中被“放大了”。除了《阿斯尔》器乐曲体裁的指向性,节目单中所阐述的历史厚重感与音乐属性的崇高性都在发生着变化。从这一点可以说地方乌兰牧骑团体在创编思想与舞台表演形式方面有革新之处。现今《阿斯尔》的表演形式,彰显出舞台综合艺术的手段,器乐曲《阿斯尔》的表演形式只是其中之一。
笔者早在2005年采访阿巴嘎旗年逾八十的原著名王府乐手玛西巴图老人时,他说:“察哈尔有《阿斯尔》,阿巴嘎、阿巴哈纳尔旗有《潮林·道》,乌珠穆沁旗有《呼格吉莫因·道》(马头琴伴奏的长调歌曲)”,这说明锡林郭勒草原内部在蒙古族总体音乐风格的基础上,各旗的地方性特殊风格是显而易见的,上述三个地区都有着各具特色的艺术表演形式,不同艺术形式的形成与各地区的历史状况、风俗习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阿斯尔》舞台艺术的综合表演手段可以理解为在当代的一种新的艺术重构吗?
结 语
近代传统音乐的发展总的来看,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保持传统音乐原貌而没有改革者,如汉族的古琴音乐和一些传统乐器合奏音乐、宗教祭祀音乐等;一种是吸收新文化、新音乐的成分,对传统音乐形式、构成有较多改进、创新,从而有较大发展者,如越剧、评剧等。随着时代的发展,《阿斯尔》原有民间器乐合奏形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上述两种发展类型都有关。
《阿斯尔》由原初的器乐合奏形态发展至今,已经变为集多种体裁为一体的舞台“歌舞乐”艺术,这不禁让人思索。可以看到,《阿斯尔》是在经历过历史上多次、多种艺术形式的重构的产物。这里涉及到《阿斯尔》的原生性与次生性的关系问题,也涉及到传承与创新以及音乐的美学本质问题。我们怎么样继承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这里所说的“继承”,应该是在保留原有本质与特色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总之,当今的舞台艺术表演的“显性”形式要与传统音乐的体裁定位、时代角色、学界的理论成果等诸多内在“隐性”的因素相契合,方能更好地继承与发展蒙古族古老的音乐遗产。
文章来源:2019“察哈尔文化·乌兰哈达论坛”论文集
编辑/吴晓倩
审核/都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