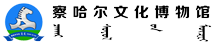编者按:何学慧,女,汉族,集宁师范学院政史系教授,察哈尔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内蒙古察哈尔文化研究会会员。
研究成果:多次主持和参与察哈尔文化研究有关的课题。发表论文《对乌兰察布开荒与退耕政策的历史考察》《清末察哈尔右翼地区的移民垦荒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新中国以来中国北疆荒漠化的政策因素分析———以内蒙古乌兰察布为例》《清代察哈尔右翼的土地政策与土地资源环境》《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放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参与论著《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路径研究》。
多年来积极参与内蒙古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各项学术活动,并在察哈尔文化“乌兰察布论坛”重要学术平台上发表了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为察哈尔文化研究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社科普及
蒙古包在古文籍中被称为穹闾、穹庐、毡帐等,满语称蒙古人的“家”为“蒙古博”,取其谐音,俗称蒙古包。《呼伦贝尔概要》云“穹庐,满洲语曰:‘蒙古博’,俗作‘包’,误。”蒙古民族包括察哈尔人特有的典型的居住形式——蒙古包,是北方游牧民族富于智慧的杰出创造和草原文化的象征,伴随着草原牧民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岁月。
一、蒙古包的源起与发展
从考古、岩画、文献记载等资料和史证中可看出,蒙古民族居住形态的演变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了不同变化,大致经历了洞穴式屋宇、窝棚、穹庐、宫廷毡帐等发展阶段。这个发展演变过程与自然环境(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经济生产方式、生产技术进步、建筑技术成熟等密切相关。
蒙古族先民同其他民族一样,最初生活在森林和大山之中,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寻找天然的山洞来遮风挡雨,居住形态是洞穴式。由于受到山洞的限制,洞穴式屋宇渐渐地不能适应狩猎生活的需要,于是搭建起上尖下圆的锥状窝棚。这种简陋的房屋以树干为支架,用芦草、桦树皮或兽皮覆盖,最大优点是制作简单、便于遗弃。这种居住形态是古代民族处于狩猎阶段,都曾有过的生活。“由几十根木杆搭成上尖下大的圆锥状住房,是原始人移至地面生活的最初居住形式”。在今内蒙古阿拉善右旗雅布赖山一带岩画中反映了这种较原始的居住形式。
随着狩猎经济向游牧经济的过渡,经济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有所增长,尖顶窝棚的缺陷日益显现,比如空间狭小,容纳人少,居舍低矮,无法站直身体等等。于是,加以改进成为圆形拱顶的窝棚,并在圆顶下加上稍倾斜的圆形直壁支撑,相对于尖顶而言,空间扩大,又稳定牢固。随着畜牧业逐渐发展和成熟,人们掌握了毛毡技术,将羊毛加工擀制成毡,便有了覆盖毛毡的帐幕。这就是最早的蒙古包,被称作“毡帐”和“穹庐”,比窝棚保暖性好,易于搭建拆卸。
蒙古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汉书•匈奴传》中有“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的记载。“穹”是指外形像天空那样中间隆起而四周下垂,“庐”在古代是指搭建在田野上的庵棚一类的居所。另据西汉桓宽在《盐铁论•论功》中记载,匈奴穹庐“织柳为室,毡席为盖”可知,匈奴的穹庐是由柳条和毛毡制造而成的室和盖两部分组成,是草原民族的居舍。
公元13世纪蒙古帝国和元代初期,蒙古人将蒙古包的制作发展到极高水平,出现了宫廷式的大型蒙古包,是其发展最为辉煌时期。宫帐蒙古包是大汗、后妃和上层王公贵族的居所,也是施政、设宴、会客、举行宗教礼仪等活动的场所。深广可容数千人,宽度可达30英尺,运载的车辆轮间的宽度为20英尺。当帐幕放在车上时,两边伸出车轮之外至少各有5英尺。用来承载这座帐幕的车辆至少需要22头犍牛才能够拉得动。装饰豪华奢侈,毡帐上下除用毛毡包裹外,还有用虎皮、豹皮、狮子等猛兽的皮毛苫盖,帐内用貂皮、猞猁皮、海獭皮等各种贵重的皮毛装饰,门槛与柱皆以金丝缠绕包裹,金碧辉煌,华贵至极。故又称“金殿”。这是蒙古族集诸北方游牧民族传统居住形式之大成,并加以创新的结晶,其工艺精湛、气势恢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至今坐落于鄂尔多斯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陵,仍保存着这种宫廷风格。
草原牧人日常使用的普通蒙古包,其形制在《多桑蒙古史》中有记载:所居帐结枝为垣,形圆,高与人齐。上有椽,其端以木环承之。外覆以毡,用马尾绳紧束之。门亦用毡,户向南。帐顶开天窗,以通气吐炊烟,灶在其中。天窗“陶脑”出现,蒙古包的形制愈加趋于实用和美观。正如《蒙古民族毡庐文化》所述,蒙古包这种古老的建筑,经过历史长河的冲刷,虽然在造型、功能上日臻完善,但却把原始建筑的构造形态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是蒙古包以外的其他建筑所很少见到的。它成为草原文化极具特质的标志物,永远传承着游牧文化的特征。
二、蒙古包的空间分布和计时功能
蒙古包的空间方位有着特定的文化形态或习俗。一般分为中央、北侧、右侧、左侧和门侧,其中北侧又分为西北侧、正北侧、东北侧。不同方位的坐卧和摆设都有固定的位置及相应的礼仪和规矩。据《绥蒙辑要》载:“蒙古包之内,除中央一部铺毡子,富者则于正面设高座,入其包内,右方为男居所,来客于此处入坐席为礼。正面稍左,斜置木柜,其上供佛像,前设佛具、乳肉,以黄油点小铜灯,此为‘圣坛’,朝夕礼拜无缺,卧时无以足向上者。妇女之居所,设于左方,此处置纳贵重品之大小柜及庖厨器皿、水桶、食料等品。中央之空地设置铁炉,高约数尺,中燃兽粪,或炊,或取暖。”
火煁(图拉嘎)是蒙古包的中央位置。蒙古人供奉和崇拜火,传说火是天神“腾格里”给人类的赐予,它永远都是包内空间关系的中心坐标,家庭的全部生活都围绕这个中心进行。火煁北侧是蒙古包最尊贵的位置,正北侧是老人或户主的专位,西北侧是神圣的供桌,专门用来供佛拜祖,是一个家庭崇奉的神龛所在。过去信奉萨满教时,将萨满的一些神偶和神祗供奉在这里。后来信奉佛教,佛龛就设在这里。
蒙古察哈尔人崇西尚右,“西向为上”。火煁西半部即右侧代表神圣和高贵,是男性专属场所,放置男子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如弓箭、猎枪、马头琴等,马鞍、马具等置于西南方向;东半部即左侧是女性活动的区域,女人的日常生活物品,如衣物、首饰及化妆品等都要置于此,生产劳动时所使用的奶桶、碗橱、炊具等放在东南方向位置。如有客人来访,男性一般要坐在西侧,女性一般坐在东侧。这种物品摆放和座次分配的有序,使蒙古包在空间不大的条件下,形成其实用性很强的特点。
蒙古包外的东西也不能乱放。勒勒车要放在包的西边,牛鞅子和牲线不能着地,要把车辕顶起来放。牛粪车放在蒙古包的西南,要放的远一点。水车放在东南,要放的近一点。灰堆设在较远的东南方向,灰不能乱倒,灰堆上也不能倒杂物。蒙古察哈尔人空间居住习俗的内外有序,是对无规矩不成方圆的一种社会公德的反映,亦表现了蒙古民族适应自然、与之和谐相处的生存理念。
蒙古包本身就是一个日晷,这是其他任何居住形式所不具有的功能。蒙古族人民通过对日出日落的长期观察,利用太阳照进蒙古包的日影计算时间。最早普遍使用的是4片14个头哈那、60根乌尼(门头上有4根乌尼)的蒙古包,2根相邻乌尼的夹角为6度,准确的形成了12个小时,这与现代时钟的刻度完全相一致。
这种计时方法通常又与12地支表示法结合起来使用,用来划分时辰。计算时辰从虎(寅)时(6点)开始,依次是兔(卯)时(8点)、龙(辰)时(10点)、蛇(巳)时(12点)、马(午)时(14点)、羊(未)时(16点)、猴(申)时(18点)……蒙古包利用日晷计时的形成,是游牧民族认识天体运行规律的智慧结晶。
三、蒙古包的特征
为适应蒙古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所从事的游牧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蒙古包在结构、形状和用途等方面,形成了独有的特点。
第一,蒙古包适应自然环境的特征。蒙古高原地处内陆,自然条件较为艰苦。夏季酷热,冬季寒冷,无霜期短,气候多变,经常遭受雨雪风暴的袭击。蒙古包光滑浑圆的外形,无棱无角,呈流线型,承受力最强,对风的阻力最小,可以有效地减缓风雪和沙暴的冲击力,形成极好的稳定性。如遇暴风袭击,还可在蒙古包外底脚压石块,或将重石块等用坠绳拽住,一顶蒙古包可以经受十级大风的考验。
蒙古包外覆盖苫毡和苫布,通体发白,有较好的反光作用,具有冬暖夏凉的特征。冬季为抵御严寒,可多覆盖几层毛毡。毛毡密度高,风难以穿透,较砖木结构的房屋保暖性强。夏季天气炎热,可覆盖1—2层毛毡,或将围毡边撩翻起来,使包内前后通风,更加凉爽。地面铺有地毡,地毡的下面铺有一些生牛皮或生马皮,具有很强的防潮作用。
第二,蒙古包便于游牧生活的特征。蒙古包是适应游牧民族的需要而产生的。游牧民族是一个游动性较强,缺乏固定地域观念的民族。由于游牧经济对气候的依赖性,必然造成大规模的、远距离的迁徙,而蒙古包制作简单,搭建、拆卸较为便捷,极适宜游牧生活搬迁。蒙古包木架结构部分均可分解,例如,哈那在搭建时将其拉开便成圆形的围墙,拆卸时将其折叠合回体积缩小,又能当牛、马车的车板。一顶蒙古包只需要两峰骆驼或一辆勒勒车就可以运走。两三个小时就能搭盖或拆除一座完整的蒙古包,妇女亦能胜任,非常适合常年迁移的游牧民居住和使用。此外,草原上包与包之间相去甚远,毛毡具有不完全隔音的特点,有利于夜间觉察到外面牲畜的动静,适应游牧生活。
第三,蒙古包满足多种用途的特征。蒙古包建筑造型呈圆锥形加圆柱体结构,与同样面积的方形相比,容量更大,实现了空间最大化。外形看起来很小,但包内使用面积却很大,一户5—7口的人家完全可以在一个5片哈那的蒙古包中生活。一个蒙古包就是一个家庭。蒙古包既是牧人日常起居饮食的场所,又是大型活动时待客的宴会厅,亦可储存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等物品,具有用以满足草原生产和生活多方面需求和用途的特征。
第四,蒙古包保护生态环境的特征。蒙古包是取自天然又回归天然之居所,以它的环保、简约、实用的建筑风格特征,成为适应草原环境和游牧生活的重要物质文化,对于草原生态环境起到了保护作用。建造蒙古包的材料均可就地取材,源自于天然。制作木架的松木及柳木常年生长在草原上,只需砍伐它们的树枝即可,伞形之骨架由柳条编制而成,不需连根拔起;毛毡是用草原上最不缺的羊毛擀制而成;绳索用驼毛、羊毛、马鬃等搓制,所用的原材料均是当地的物产或畜产,不用工厂加工,不产生废水、废气、废碴等,对环境无任何污染。这是现代的任何建筑,都无法比拟的。
同时,在搭建蒙古包时更不会对草场资源造成破坏。因为不用破土打地基,只需割去地面上青草,不会对草根受到任何破坏。牧民亦不会长期居住于同一地方,迁移后不会留下污染物,不久又会青草满地,对草原生态环境无丝毫破坏,也体现了游牧文明的万物皆有灵的生态价值观。
四、蒙古包的象征习俗
第一,完满的象征。从蒙古包的形状角度来看,整体造型取自于“天”呈圆形。分解来看,陶脑是圆形,火煁是圆形,围圈起来的哈那也是圆形。从美学上讲,体现着审美取向。古希腊美学家毕达格拉斯认为:一切立体圆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在蒙古民族的观念中,圆形历来被视为完整、完满、完美的象征意义。“圆形是本身最单纯的完满自足的、凭知解力界定的最有规律的线形。”在无垠浩瀚的草原,这种单纯的完满自足的线形与笼罩四野的苍穹相和谐,乳白色的蒙古包与绿色的大自然相照应,显示出蒙古民族素朴单纯之美,折射出其传统的审美观念。此外,“天似穹庐”的居所,蕴含了游牧民族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价值观念。
第二,兴旺的象征。蒙古包内部空间形成以火煁和陶脑为中心,火是天神赐予的,是祖先留传下来的火脉,预示生活像火焰一样旺盛。火煁上方正对陶脑,因其形状和实用功能与太阳有关,无论从包内太阳照射进来的立体看,还是把它用平面图形的形式体现出来,圆形陶脑与四面轩插的乌尼杆呈辐射状光芒四射,故被视为是日月的象征。蒙古包的门朝着日出的方向,这与太阳崇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好印证了蒙古族视太阳初升为吉祥和兴旺发达的象征这一习俗,使蒙古包兴旺的象征更加明确。同时,也与蒙古民族崇日尚圆的审美心理和实用价值需求是完全吻合的。在英雄史诗中,当讲到英雄的居所时,蒙古包既高大,门又朝着太阳;而英雄对立的恶魔——莽古斯的居所的门朝着西北方向,预示了邪恶、黑暗,这与蒙古族人的思维观念,及对善恶的理解都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美好的象征。蒙古包的覆盖物毛毡是用洁白的羊毛擀制而成,这既与草原上盛产绵羊有关,也与蒙古族审美意识崇尚白色有关,他们视白色为圣洁、崇高、美好的象征。女儿出嫁时一定要给她搭建崭新的洁白的蒙古包。普通的蒙古包,经过一段时间的风吹日晒后,毛毡旧了颜色会逐渐变黄,每隔三年五载就会重新置换。通过不断地更换毛毡,蒙古包永远都是非常美丽的、圆润的、洁白的。蒙古包的洁白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和主人的持家能力。在蒙古人心中的美好愿望就是把自己居住的毡包变得更白,实际上是寓意着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富裕丰足、美满幸福。因此,不论是从美学观还是实际生活需要出发,洁白的蒙古包具有崇尚富裕美好的象征意义。
蒙古包及与此相关所产生的一系列居住习俗,是蒙古察哈尔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草原牧人的精神寄托,蕴含着游牧民族的无穷智慧。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历史的发展,蒙古察哈尔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蒙古包作为蒙古民族标志性的建筑,已在察哈尔南部、土默特及东部地区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汉式土坯房、砖瓦房。因此,保存和传承蒙古察哈尔传统文化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弘扬和发展蒙古察哈尔传统文化为中华多元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文化动力。
文/何学慧
文章来源:2017“察哈尔文化·乌兰察布论坛”论文集
编辑/吴晓倩、赵越
审核/温都苏
摄影/刘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