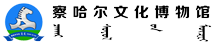编者按:薄音湖,著名蒙古史学者,曾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现为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内蒙古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学术顾问。
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元史,专门史·中国民族史,侧重于明代蒙古史的研究,出版《简明古代蒙古史》、《一代天骄和他的继承者》、《元太祖本传》、《明代蒙古史论》等专著,出版了古籍整理《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二辑。发表论文《达延汗生卒即位年考》、《俺答汗征兀良哈史实》、《俺答汗征卫郭特和撒拉卫郭尔史实》、《俺答汗征卫拉特史实》、《十六世纪末叶西藏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关于北元汗系》、《关于察哈尔史的若干问题》、《明代蒙古的黄毛与红帽兀良哈》、《买的里八剌与脱古思帖木儿》、《明美岱召泰和门石刻考》等50余篇。
数十年来,他始终在蒙古史的教学科研岗位上勤奋努力、耕耘不辍,为蒙古史研究倾注心血,为国家培养人才竭诚尽力。多次受邀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论坛,接受国内外各级媒体的采访报道,在传承弘扬察哈尔历史文化,抢救保护珍贵文化遗产,繁荣发展民族文化事业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受到了各级领导高度赞誉和国内外学者的爱戴。
社科普及
明代蒙古中兴君主达延汗(Dayan qaγan,1474-1517)在十六世纪初统一东蒙古后,建立了六万户,并分封诸子为各万户及万户之下各鄂托克的领主,由此确立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对全蒙古的牢固统治。察哈尔(čaqar)是六万户之一,亦即大部落集团的名称,直属大汗,其地位崇高,势力强盛,在政治和军事诸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由于史料的限制,对于察哈尔的研究尚远不够充分,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就有关的若干问题继续进行探讨希望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一、察哈尔的起源
察哈尔是入清之后对这一蒙古部落名称的汉译,沿用至今。它在明代汉籍中有多种译法,最早见于嘉靖二十年(1541)成书的《皇明九边考》,作“察罕儿”,稍后以同样的形式见于《明实录》嘉靖二十五年,后来的史籍又作“擦汗儿”、“叉罕儿”、“插汉”等。在蒙文史书中,察哈尔一名出现于著名的瓦剌太师也先专权时期的记载中,时值明正统、景泰年间(1436—1456)。据说达延汗的祖母齐齐克拜济(Sečeg Beyiǰi)生子巴延蒙克(Bayan Möngke,达延汗之父),为使儿子免遭也先的杀害,将察哈尔(čaqar)的呼拉巴特鄂托克(Qulabad otoγ)的妇人鄂推(Otoi)之女放于摇车内,替换巴延蒙克,瞒过了也先派来侦伺的人。
由此可知,在十五世纪中叶至十六世纪中叶,察哈尔已作为部落名称闻名于蒙古和汉地了。以常理推论,察哈尔的起源显然应该早于这个时期,但由于没有直接的史料,进一步追溯其起源十分困难。法国的伯希和曾从语言学的角度做过推测,日本的冈田英弘从史实的角度做过探讨。问题得到更清楚的说明。
按照冈田英弘的研究,瓦刺太师也先称汗后不久死去,随后是马可古儿吉思 Markörgis)、摩伦(Mulan)满都鲁(Manduγulun-Mand uγuli,1475-1479年在位)相继称汗。满都鲁是达延汗的曾叔祖父,他是已知的最早君临察哈尔万户的蒙古首领。满都鲁死后,他的遗孀满都海彻辰哈屯(Manduqai Sečen qatun)继承了察哈尔部众。满都海出身于土默特(Tümed)的恩库特(Enggüd,即汪古惕)她后来嫁给了巴图蒙克达延汗。达延汗通过与满都海的联姻,握了满都海已故前夫的私产察哈尔和满都海娘家的部落土默特,其根据有《黄金史》中的一段记载:“达延汗统辖察哈尔和土默特两部,一起去征白乙加思兰,虽然这段记载的年代有误,但反映了达延汗早期即已掌握了这两个部落的事实。
冈田英弘关于察哈尔是由满都鲁汗经满都海哈屯而传到达延汗之手的结论,确有相当的道理,只是论据未能充分展开而已。事实上还可举出不少相关的例证。例如,满都鲁汗死后,成吉思汗长弟合撤儿的后裔乌讷博罗特王( Ünebolod ong)向满都海求婚,满都海回答说:“你合撒儿的后裔想得到我可汗的遗产(öb)吗?”而当满都海向扎哈阿海(ǰ aqan aqa)询问是否应当嫁给乌讷博罗特王的时候,扎哈阿海劝告满都海:“若是嫁给合撒儿的后裔……就远离了你所有的国民( qamuγ ulus)……若是嫁给可汗的后裔……就主宰你所有的国民……统御起察哈尔万户(čaqar tümen)。这段故事说明满都海确实从已故前夫满都鲁汗那里继承了察哈尔万户,如果她想继续统治这个万户,就必须拒绝合撒儿后裔的求婚,而保持成吉思汗直系后裔的哈屯的身份。又如,达延汗的生母锡吉尔太后(Šikir tayiqu)曾被亦思马勒太师(Isman tayiši)掳去为妻,达延汗即位后,遣托郭齐实古锡(Toyoči Šihuši)击杀了亦思马勒,但锡吉尔不愿回到儿子身边,于是托郭齐怒斥她说:“你的儿子可汗不好吗?你的百姓察哈尔不好吗?”强迫她上马。显然,这时的达延汗已经通过与满都海结婚而统辖了察哈尔万户。
是否还可以继续上溯察哈尔的由来呢?冈田英弘在他的研究中,没有提到察哈尔部名在满都鲁汗之前的也先时代即已出现的情况,但他反复论证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察哈尔是对神圣的女祖先、拖雷之妻唆鲁禾帖尼崇拜的部落,而唆鲁禾帖尼曾被成吉思汗赐以八鄂托克察哈尔万户(naiman otoγ čaqar tümen)。事见罗卜藏丹津《黄金史》。据说成吉思汗患病时,其幼子拖雷也感不适,卜者说,如果其中一人痊愈,另一人将难逃厄运。于是拖雷之妻察兀儿别吉(čaqur beki)向上天祈祷说:“如果汗主死去,全国人民都将成为孤儿,如果拖雷死去,只有我一人成为寡妇”。她的祈祷果然应验,拖雷死了,可汗痊愈。为此成吉思汗嘉奖儿媳察兀儿不顾丈夫、敬重汗父的贤德,特给以封号,并赐予她八鄂托克察哈尔万户。
《黄金史》的记载没有其它史料可为佐证,而且有明显的错误。一是传说中拖雷并非替父成吉思汗而是代兄窝阔台而死,史载1232年拖雷随太宗窝阔台征金,太宗患病,拖雷祷于天地,请以身代之,又饮巫师之水,不久太宗病愈,拖雷死去。二是拖雷之妻是克烈部王汗之弟札合敢不之女唆鲁禾帖尼,察兀儿别吉乃是王汗之女。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出现了“察哈尔”一名,尤使人感到突兀。由于这些原因,札奇斯钦断言《黄金史》的记载完全是“后人的臆作” 。
“八鄂托克察哈尔万户”确实是明代蒙古达延汗时才出现的社会组织,但是“察哈尔”一名恐非《黄金史》作者的“臆作”,它可能在成吉思汗时代即已存在,其来源或可远溯至唐代。
活跃于隋唐时期的突厥汗国拥有大量军队,其军队的组成,有被称作“附离”的待卫之士,有从突厥各部征集来的控弦之士,还有由中亚昭武九娃胡组成的精兵,这些精兵被称作“柘羯”。唐贞观四年(630)大将李靖出击东突厥,吉利可汗兵败被执,东突厥政权亡,“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来降者甚众,酋豪首领至者皆拜将军,布列朝廷,五品能上能下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柘羯不至,诏使招慰之”。这是“柘羯”较早见于史书的一例。一百多年后的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叛唐,唐玄宗仓猝防御。当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正在朝廷,慨然请战,玄宗便任命他为范阳节度使,到东京(今洛阳)募兵。封常清十天之内募兵六万,固守东京。所募的士兵中,也有被称作“柘羯”的军队,参与了与叛军的战斗。《旧唐书》载:“(天宝十四年)十二月,禄山渡河,陷陈留,入甖子谷,凶威转炽,先锋至葵园。常清使骁骑与枯羯逆战,杀贼数十百人”。叛军之中也有柘羯军。唐将张巡等人睢阳(今河南商丘),安禄山之子安庆绪遣尹子琦围城,“有大酋被甲,引柘羯千骑麾帜乘城招巡”,张巡设伏解围。后来潼关、西安相继陷落,玄宗之子肃宗调集朔方、陇右、河西、安西诸镇和西域、回纥的人马,夺回了西安和洛阳,西来的西域土兵中,亦有柘羯军。杜甫作于至德二年(757)的《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中记述当时情景说:“花门腾绝漠,柘羯渡临洮,此辈感恩至,赢俘何足操”花门指居延海北的花门山堡,在这里作为回纥的代称,回纥腾漠而来,柘羯则自西渡临洮而来。
在唐代如此活跃的柘羯,其语源、语意是什么呢?《新唐局》叙昭武九姓之一安国情形说:“大城四十,小堡千余。募勇健者为柘羯,犹中国言战士也”安国一作布豁,又作捕喝,即今之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玄奘《大唐西域记》叙另一昭武九姓之一飒秣建国时,以柘羯作“赭羯”,“兵马强盛,多诸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飒秣建又作萨末革建,一称康居、康国,即今之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因此,柘羯是当时中亚诸国募集的军队的名称。其读音依照《广韵》是:柘,之夜切、章母、马韵、开口三等、去声、在假摄,拟音为[tφǐɑ];赭,章也切、章母、马韵、开口三等、上声、在假摄,拟音亦为[tpia];羯,居竭切、见母、月韵、开口三等、入声、在山摄,拟音为[kǐet]。隋唐时代,常以t收声的入声字来译写别族语言以r结尾的音节,因此kǐet(羯)所表示的实际发音应是[kǐer]。
日本白鸟库吉、堀谦德都认为柘羯为东厥语sagas之译语,战士之意。法国沙畹认为“柘羯、赭羯,皆为波斯语 tchakar之同名异译,此名在康居一带训作卫士”。伯希和将波斯语čakar(意为仆人)与蒙古语“察哈尔"(čakhar)联系起来,认为后者源于前者,并认为波斯语进入蒙古语,在词义与语音两方面都相应,毫不奇怪。芬兰兰斯铁则认为作为蒙古语的可чakap(察哈尔)一词,表示的意思是“王公宫廷周围的平民(工匠、仆人等)”。
按照上述,大体可做如下推测:波斯语 čakar至少在唐代就已在中亚流行,被当作募集的军队的名称,此种军队随突厥统治者进入中国,以柘羯( tφǐa kǐet) 载人史书,这个词在唐以后仍然存在于蒙古高原,蒙古兴起后成为蒙古语词 čaqar(察哈尔)并流传下来,如果这样的推测可信,那么蒙古语“察哈尔”一词是有其久远的历史渊源的。
“察哈尔”的蒙古语词意,仍然如《新唐书》所言,表示“战士”的意思。大约成书于十七世纪初的《大黄册》所载达延汗六万户的赞词,就说:“利剑之锋刃,盔甲之侧面,这是察哈尔万户”。在鄂尔多斯流传下来的成吉思汗祭词中,关于察哈尔颂歌的内容也大体如此。赞词和祭词表现的察哈尔形象,正是勇猛的武士。赞词和祭词关于永谢布(永谢布加上喀剌沁、阿速特为一万户)曾为蒙古贵族提供“马奶佳酿”的记述,有很高的正确性,我们认为,关于察哈尔的记述,也同样反映了蒙古人对这一词语的准确记忆。
现在再来分析拖雷之妻唆鲁禾帖尼被成吉思汗赐予“八鄂托克察哈尔万户”的传说。毫无疑问,这是将明代才出现的达延汗直属万户的名称“八鄂托克察哈尔”原封不动地上移到蒙古帝国时期,不足凭信。但是其中的“察哈尔”或许并非完全的虚构。我们是否可以猜测,成吉思汗曾经赞赏儿媳的贤惠,特意赐给她若干察哈尔—战士呢?给亲族分拨军队,本来是帝国财产分配的主要内容。遗憾的是,除了《黄金史》的传说之外,我们找不到当时的记录。但是,正如冈田英弘指出的那样,察哈尔与唆鲁禾帖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的关系或许有助于说明历史传说的真实性。
《黄金史》记载说,有一天成吉思汗忽然而生对宗教的信仰,便派人到西藏给萨迦满珠习礼喇嘛送信,希望能有一位菩萨在自己的子孙中转世。喇嘛给信使一只金匣子,并嘱咐说:“不要开启,把它带给成吉思汗。他的一个儿媳是菩萨的化身。举行一个盛大的祈祷法会,让名为苏曼达里( Sumandari)的儿媳开启观看。”在鸡年正月十五日,成吉思汗举行盛大的祈祷法会,让拖雷之妻也失哈屯( Eši qatun)开启那金匣,里面有三只金蚊子,这些金蚊子飞进也失哈屯的鼻孔,进入她黄金般的胞胎,十个月后,在哈喇和林生下了转轮王的化身忽必烈薛禅汗和阿里不哥二人。
由此可知,拖雷之妻唆鲁禾帖尼也被称作也失哈屯。她作为建立元朝的国君忽必烈之母,受到特别的尊崇。她是一位基督教徒,死后被祭祀于基督教堂。《元史》载,1335年(后至元元年)“中书省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于内,请定祭礼’。从之”。所谓十字寺即基督教堂。
元亡后,忽必烈的子孙仍然恪守奉祀也失哈屯之礼,其证据是《蒙古源流》和《黄金史》提到的满都海向也失哈屯的祈祷。据说满都海拒绝了合撒儿的后裔乌讷博罗特王的求婚,决定嫁给忽必烈的后裔巴图蒙克达延汗时,曾在也失哈屯的灵前祈祷,表示她要扶持巴图蒙克的决心,并祈求赐给她七男一女。满都海是满都鲁汗的遗孀,这件事表明了也失哈屯以前是由满都鲁汗奉祀的。
达延汗之孙博迪汗继续奉祀也失哈屯。博迪汗既是全蒙古的大汗,也是左翼察哈尔万户的直接统治者。《俺答汗传》在记载1538年蒙古各部征讨兀良罕时,说右翼诸万户在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和俺答汗的率领下,携带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驻扎在杭盖山阳,左翼诸万户则在博迪汗的率领下,携带也失哈屯的神位驻扎在杭盖山阴。显然,也失哈屯的神位应当在博迪汗所在的左翼察哈尔万户之中。
察哈尔与也失哈屯的密切关系,说明了成吉思汗赐予唆鲁禾帖尼“察哈尔”一事的可能性。
至此,关于察哈尔的起源我们似乎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明代蒙古察哈尔的得名,也许与蒙古帝国时代成吉思汗赐予唆鲁禾帖尼的军队的名称有关,即当时就可能称作“察哈尔”。这一名称又源于唐代突厥军队的一种一柘羯,名词来自波斯语,意即仆人,借入突厥语后意为战士,再转入蒙古语,仍是战士之意。
以往的研究中,对察哈尔的解释有几种。一是“邻近”之意,理由是蒙古语“札哈”(ǰap-a)意为“边界”、“边境”,察哈尔部的驻牧地毗邻长城,所以察哈尔( čaqar源于此词。一是“白色”之意,因为蒙古语“察罕"(čaγan)意为白色,察哈尔源于此词。是“孩儿”之意,《元朝秘史》第68节“察合”旁译为“孩儿”,这个词来自突厥语čaqa——小孩子,察哈尔或者来源于此。我们知道,明代察哈尔万户的驻牧地先是在今锡林郭勒盟一带,后来东移到黄河(西拉木伦河)中游地区,入清之后察哈尔八旗才迁至今张家口、大同的长城边外,因此“邻近”长城之说并无根据。其它两种说法也是从词语相近而做的推测,但需要进一步的史实来论证。
待续……
文/薄音湖
文章来源:《察哈尔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编辑/吴晓倩
审核/温都苏
摄影/刘立志